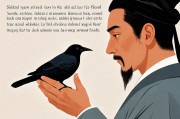父亲死第二次的那个夜晚,灵堂的烛火竟比生前更亮,我站在送葬队伍之首,捧着同一只骨灰盒——它比记忆里沉了三分,大约是吸纳了生者额外的泪水,棺木入土时,我忽然听见泥土下传来指甲抓挠木板的声响,凄厉得使送殡的白菊瞬间蜷缩成拳头,我惊醒,冷汗浸透的睡衣紧贴脊背,窗外仍是那片不肯变亮的墨色天空。
这绝非独属于我的荒诞剧本,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幽暗舞台上,死亡从来不甘于一次性的简陋演出,它要返场,要加戏,要在生者的颅骨内剧场强行安插续集,那些理应安息的亡魂,偏要踉跄爬回我们梦中,把悲剧重演,把丧钟再敲,把未流的血在我们眼皮底下再淌一遍,这哪里是梦,分明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性谋杀——谋杀了我们对“终结”的幼稚幻想。
原始部落的萨满早看透了生死间的薄幕,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将祖先颅骨供奉于屋梁,并非出于瘆人的趣味,而是深信死亡需经三次腐化——肉体之死、社会关系之死、记忆之死——方得圆满,非洲多贡族则为逝者举行“达玛”祭礼,意在将彷徨人间的游魂强行推往来世,防止其因眷恋而频频返场搅扰生者,可见古人深知,死亡从非一锤子买卖,而是层层蜕皮的漫长仪式;今人自以为是的“科学死亡观”,在梦的原始暴政前不堪一击。

我们被囚禁于线性时间观的牢笼,总一厢情愿地认定死亡是刻度分明的终点站,但亡灵偏要踏碎这幼稚的时空秩序,他们在梦的混沌领域中肆意穿梭,把生与死的标签搅成一锅粥,那梦中再死的亲人,表面是恐惧的投射,实则是生者与亡灵合谋的哑剧——我们借这场自导自演的二次丧礼,试图完成第一次未能兑现的告别,或是偿还拖欠的泪水与忏悔,这无异于一种时间的巫术,我们在清醒世界被剥夺的补救权,终于在梦境里篡位成功。
现代社会将死亡消毒、隔离、包装成一次性事件,我们被迫压抑悲恸,强作镇定,但未被超度的哀伤岂会乖乖就范?它们潜伏在心理暗舱,最终在梦中炸裂成一场更诡谲、更暴烈的死亡仪式,那口梦中棺椁,既是 Freud 所言“被压抑者的回归”,更是 Marc Augé 所指“非场所”中的身份焦灼——我们在现实丧礼中来不及定位的悲伤,只能在梦的超现实空间里仓皇彩排。
我逐渐疑心,梦中再死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位亲人,丧乐哀切,幡幢摇动,躺在灵柩里的分明是昔日与死者相伴的某个自我,我们借亡灵之躯,为旧我送葬;借虚幻的哭声,悼念实际逝去的年华,这是生者阶段性的自我清理,如同蛇定期蜕皮,蝉果断弃壳。
直至某个午夜,父亲第三次踏入我梦境,没有丧服,没有棺木,他只倚门轻笑,衣角沾着蒲公英,我顿时了悟前两次葬礼的隐喻:第一次埋葬的是他的呼吸,第二次埋葬的是我的执念,而此刻,他不过是顺道探访,如风路过树林,不索取一滴眼泪。
人类文明建构的死亡叙事何其脆弱,夜复一夜被梦的潮汐轻易冲垮,唯有承认亡灵有权在我们的精神领土反复生灭,有权要求一场又一场缥缈的丧典,我们方能在虚与实的裂隙间,与那些永不真正逝去的魂灵达成微妙和解,每个梦见逝者再死的人,不过是在内心剧场默默补办一场迟来的仪式,好让生与死这两大敌对阵营,在暗夜中短暂地、象征性地签署停火协议。